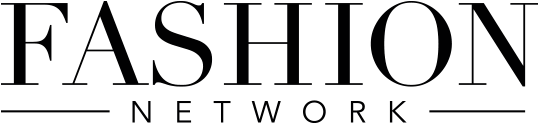时装月如火如茶的上演着,T台既是下一季度订货的风向标,亦是舆论与流量的放大镜,它把一切光鲜亮丽的搬到台上,而把琐碎的、含糊不清的都置于台下。今年,各个品牌不约而同地把“东方主义”大肆舒张,是抄袭、是致敬?恐怕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一直憧憬着实现自己的大国梦,其历任领导人和政治领袖,也都在努力探索适合印度的大国发展之路。作为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曾在1943年对印度的大国梦进行过如此阐述:“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
”姑且不论当代印度的政治取向与大国竞争,印度确实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它的经济地位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与提高。与此同时,在今年的T台之上也见到了以印度为基础的“东方主义”趋势的抬头——或曰,借尸还魂。
几个世纪以来,在文学、绘画和音乐领域,“东方主义”一词描述了欧洲人对亚洲国家所持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表面上表现为对“东方”这一高度刻板概念的审美迷恋,在这种概念中,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认同被错误地归为一类。正如巴勒斯坦立国运动的积极分子、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70年代所定义的,它指的是通过审美化来重现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对立的意识形态构想,轻视和歪曲它们所声称描绘的文化。

在上个时装月(米兰和巴黎时装周)期间,这一术语再次出现,因为各种时装秀中明显出现了一些设计元素,显然借鉴了几个南亚和西亚国家的传统服饰——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正是奢侈品行业为了寻找中国市场的替代品而试图吸引的国家,其中尤以印度和阿拉伯半岛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这一问题在Prada的案例中尤为突出,尽管Prada上演了一个基本中性的系列,但亮出了与印度传统Kolhapuri凉鞋几乎相同的凉鞋后,遭到了印度工匠协会的抗议,随后此时泛起涟漪,一度扩大至印度前国会议员兼Kolhapur地区古老王室成员Sambhaji Chhatrapati下场呼吁,他称此事件为“新时代殖民主义”。随后,品牌官方很快以正式信函的形式向马哈拉施特拉邦商会道歉,信函由Miuccia Prada之子、Prada集团执行董事Lorenzo Bertelli签名。尽管这个孤案只是本季的惊鸿一瞥,但放大到整个时装月的主流品牌系列之中,都能见到模糊而谨慎地致敬了各个亚洲国家的传统设计。
在分析有多少以及哪些元素被提及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个品牌都保持着极其谨慎的态度,只进行微妙的暗示,从未涉足直接的挪用——否则肯定会遭到相关人士的谴责。例如,杰尼亚(Zegna)在迪拜的秀,直面演绎了“中东沙漠世界的烈日酷暑”;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将当代印度多元感性如面料、剪裁、色彩和工艺,与城市、自然和阳光活力进行联系。需要澄清的是,它们并没有试图模仿这些国家的服饰,而是试图唤起相关的氛围情绪——尽管如此,杰尼亚的尼赫鲁衬衫、路易威登受《穿越大吉岭》启发的包袋,以及它们系列中的睡衣条纹(“pajama”这个词源于波斯语)和其他一些设计元素,似乎都试图与印度和阿拉伯半岛的观众牵起手直接对话。

除此之外,还有Emporio Armani、IM Man、Qasimi和Prada等,不约而同都出现了长款无领衬衫,类似于经典印度Kurta的混合版本;而在法国品牌Jacquemus,一些造型让人联想到海湾国家常见的thawb束腰外衣和taqiyah帽的组合;Bluemarble则以更传统的长衫为特色;在Valentino的2026年度假系列中,绒面革djellaba再次出现,通过一系列衬衫搭配几何装饰背心,隐约让人联想到印度时尚和贝都因人服饰的混合;Dries Van Noten腰间系着彩色腰带,让人联想到它会被用来束住也门双刃匕首(Jambiya),它活脱脱就像19世纪摩洛哥精美的希扎姆(Hizam)腰封,穿越历史与沙尘而来;在同一场秀中,还出现了类似纱笼一般宽松肥大、装饰华丽的矩形织物。无独有偶,这种真丝织物也出现在Junya Watanabe的秀中。
若非我们谈论“东方主义”,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设计元素都逐渐在记忆中退却——无论是衣领、像纱笼一样佩戴的围巾、套在裤子外面的束腰外衣衬衫,还是衬衫和印花背心的组合,似乎唤起了一种模糊而遥远的地平线——几乎就是维多利亚时代作家惯用的殖民化术语“东方”所指的那个遥远、神话和想象中的土地。在这个虚构的国度之中,印度、东南亚、北非和阿拉伯之间的轮廓界限变得模糊,变成了一种在我们脑海中与所有神话起源故事一般等距的幻想。


早在1977年年,正当壮年的Yves Saint Laurent在秋冬季发布会上首度展出了一个名为“La Chine Impériale(中华帝国)”的高级定制系列,它美妙而又奢华的造诣成就了划时代的影响力。同年,他又无中生有创造了一款名为“鸦片”的香水。他亲口说道:“我曾在梦中到达过每一个国家。”梦境成就了他的时尚奇景,尽管他此前从未去过亚洲,但对亚洲文化尤其着迷,与他的伴侣Pierre Bergé一同收藏了大量来自中国、印度、日本的各类服饰、文学作品、文物等资料,从中汲取设计元素——从日本歌舞伎到印度王公,从中国宫殿到越南斗笠,通过设计他营造出一个梦想中的东方国度。在这个系列发布的8年后,他首度亲赴中国,并通过展览、时装秀等多元途径,最终他的商业帝国在亚洲版图徐徐盛开。
因此,与其狭隘地用“殖民主义”或“文化挪用”,像二极管一般批判一切创新。不如用善意来拥抱一切开放的全球主义。毕竟,如罗兰巴特所言,服装既有着物理属性的遮蔽、保暖之用,也有着模糊而复杂的文本价值。创作者的“所指”,并非受众的“能指”,镜里看花水中捞月,在语境愈加狭窄的公众场域,所有二元对立的评价,无非都是一场空谈狂欢。
全球衣橱十方来财,意大利西装、机车皮夹克、运动鞋或乐福鞋在一个融合的数字场域中共存,不加区分地服务于世界各地。同时,创意总监们也如候鸟般地大展宏图,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时装秀的媒体影响力,让全球观众能够认出一些似曾相识的轮廓。时尚的趋势与品牌的选择,往往都下意识揭示了它们的焦虑——是否有可能在亚洲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推动停滞不前的生意?但对消费者而言,时尚应当带来更多的快乐与乐趣,而非执着在曾经的“可持续”焦虑,以及当下的设计元素与标签上的产地焦虑。
Copyright © 2024 FN团队版权所有,严禁转载.